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 1045 年,大宋庆历五年,大辽重熙十四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八年。
今年宋朝最大的事,莫过于庆历新政的正式失败。标志性的事件是这么几个:第一,支持新政的宰相,晏殊是在去年,杜衍是在今年被罢相。第二,范仲淹和富弼,虽然去年就离开京城到地方工作了,但毕竟还保留了参知政事(副宰相)的头衔,但是到了这一年的 2月份,这个头衔也被拿下。第三,几项新政措施,比如什么京官要在岗位上做满五年才能升职啊,对恩荫官员的限制啊,也都在这一年的 2 月份被取消。到了 10 月,新政最后下最后的一项改革,关于保举官员的规定,也被废止。一场热热闹闹的变革,就这么烟消云散了。关于庆历新政为什么失败?其中的原委,我在1043那期节目中已经讲了。今天不再赘述。
今年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处理宋夏战争的后续问题。
上一年的年底,大宋朝终于和西夏把合约签订了下来。整个过程其实很不容易。
我们以前讲宋夏战争的时候,可能给你留下一个印象,就是大宋朝这边非常吃力,不仅总打败仗,而且也快把财政拖垮了。但是你想,打仗打的是国力啊,大宋都被拖垮了,西夏那边的情况能好到哪儿去?它的内部,军事上有叛乱,经济上有灾荒,和大宋的贸易也断绝了,茶叶、衣服这样的进口品也奇缺。而且,西夏总人口也就300多万,但是常备军有60 万,就算是草原民族亦兵亦民,那也差不多是把成年男子全都卷进去了。这样的战争是无法持续的。别说输了,就是一直胜利,打的时间一长,国家一样会垮。所以,停战谈和,这不只是宋朝一家的愿望,西夏一样也是不想打了。
这个时候就看出来西夏国君元昊的性格了。撑不下去也要强撑,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讨价还价。刚开始,他说,我能不能不称臣?但是我本人可以叫你宋朝皇帝一声爸爸。用我自己矮一辈,换来国家之间的平起平坐。宋朝这边思来想去,说不行。大宋不是跟你西夏争高低,问题是还有一个大辽,你西夏对大辽称臣,不对我称臣,动摇的是我和大辽之间的战略均衡。要谈,你就必须对我大宋称臣,这是底线条件。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就连叫爸爸这事,元昊也搞了个小把戏。他在给宋朝的国书中自称“兀卒”,说西夏语中的天子就叫兀卒,我看现代西夏文研究的学者说,确实如此,但问题是,这在大宋这边看起来就是,你叫我们皇帝一声爸爸,但我念你的称号,叫兀卒,汉语发音像是“吾祖”——我爷爷——这不把便宜又占回去了吗?这是何等的侮辱啊?我猜,这不是什么凑巧,这应该是元昊有意为之的。你来从中感受一下,元昊那种寸步不让的谈判风格。
双方就这样拉拉扯扯,到了上一年,1044年的12月29号,和平协议终于签下来了。核心就是三条:第一,不打了,第二,西夏继续对大宋称臣。第三,大宋每年给西夏一笔经济补贴。
对于大宋来说,本来也只要一个称臣的结果,恢复双方开战之前的原状就行。而用钱买和平这个代价,也不是什么新思路,能买对大辽的和平,为什么不能买对西夏的和平?
但问题是,你发现没有?这个协议是有漏洞的:西夏对大宋称臣,这是个概念,怎么落实呢?只要元昊还是西夏的君主,就落实不了啊。来往的国书,只是一小批外交人员能看到的。至于在西夏,元昊是严防死守,根本不让普通西夏人知道这回事。那你说,宋朝每次派使者去西夏,总能够宣传一下,你们西夏对我们称臣吧?事实上,后来宋朝每次派使者过去,走到边界就不让进了,从来没有去过兴庆府,西夏的都城,所以,元昊在内部还是皇帝。你看,称臣这个事,元昊在中间这么一拦,把信息这么一掐,就成了个纸面游戏。
那你说大宋这边是不是一点反制措施也没有?也不能这么说。在合约文本一大堆文字里面,一般我们不会注意到有这么三个字,叫“奉正朔”:奉是奉献的奉,正是正月的正,指一年的头一个月,朔是指一个月的头一天。奉正朔啥意思?就是西夏用宋朝的历法。你的正月就是我的正月,你的初一就是我的初一。
到了这一年,也就是公元1045年,庆历五年的11月,大宋又把这个约定凿实了一下,正式把大宋的历法,《崇天万年历》颁布给了西夏。
对历史熟悉的朋友会觉得,奉正朔,这不也就是一个仪式性的说法吗?用你的日历,又能如何呢?哎,不一样,这其中自有深意。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借着西夏奉宋朝正朔这个事,说一说这其中的深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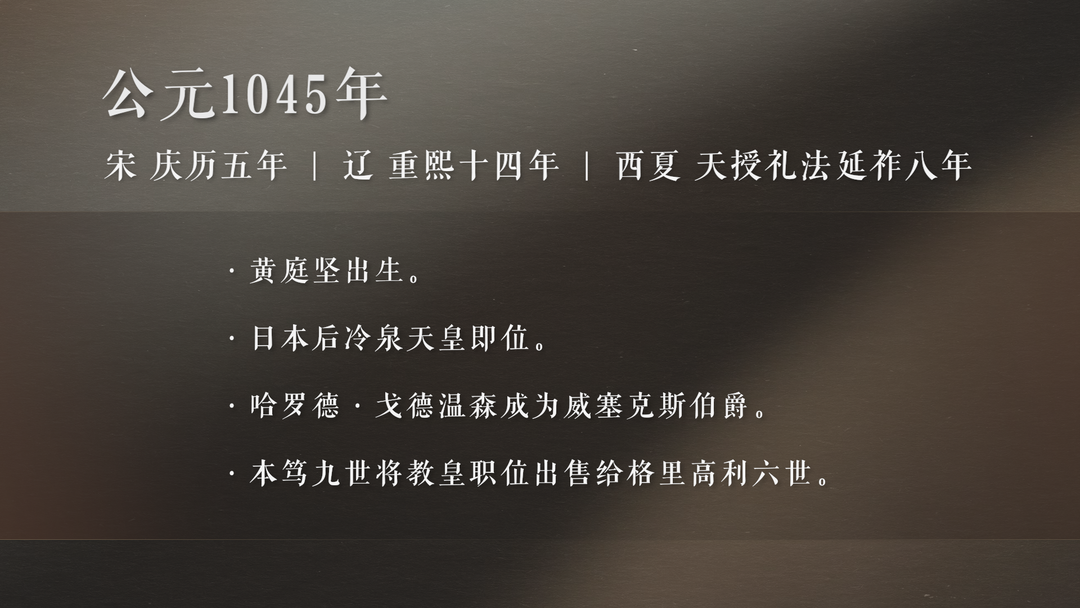
工具性的时间
西夏奉宋朝的正朔,宋朝给西夏颁赐历法,这事有那么重要吗?除了象征性的意义之外,它有实际作用吗?有。
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你是宋仁宗,现在你想对西夏的老百姓有点实质性的影响,还有什么方式?在那个时代,权力和老百姓的互动,不过就是那几样:收税、征兵、司法、救灾。只要西夏国主还在位,还在搞“对外称臣、对内称帝”那一套,这几件事,你大宋皇帝你就一点插不进手。想让西夏老百姓多少还保持一点对中原皇帝的认同,就只剩下这最后一丝缝隙,让他们在时间节奏上和中原王朝同频共振。这是绕过元昊,发挥影响力的唯一办法。
历法的本质是什么?是统一大家的时间表。这本身就是一种权力。
中国古代不是有一首《击壤歌》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站在一个老百姓的视角,我过日子要什么时间表?抬头看太阳就行了。你们那些国王君主对我有啥用?但是,你换个自上而下的视角,任何一个有权力的人都知道,一张统一的时间表是权力的基础啊。因为权力是用来组织合作的,而合作是必须建立在时间上的。
比如,你要搞祭祀,得有公认的时间表吧?大禹要召集天下的诸侯到会稽(就是今天的浙江绍兴)开会,有一个防风氏的迟到,大禹直接就把他杀了立威。你想,当时从中原各地赶到浙江,路途多远?发会议通知的时候,大禹总得说明是几月几号开会吧?而且收通知的人也得用的是同一张时间表吧?否则大禹就没有理由发飙啊。
再比如,你要搞军事行动,几月几号,大家在哪儿聚齐,分几路出发,几月几号在哪里包抄合围,都有一张公认的时间表吧?再比如,你要搞法制,陈胜吴广,朝廷征发你们去哪里当差,几月几号不到,就要砍你们的头,执行这样的法律,需要一张公认的时间表吧?
再比如,你要建设官僚制,你也需要一张公认的时间表。赵冬梅老师在这本《法度与人心》里,就举过唐朝的例子。大唐朝廷是在每年的十一月颁布下一年的历法。但因为吐鲁番跟长安隔着两千多公里,等历法传到吐鲁番的时候,都到下一年的二月了。那个时代的交通状况就这样。可问题是,地方政府给官吏们发的口粮,是按月发的,大月小月不一样。你看,麻烦了吧?有两个月,不知道怎么发。所以,只好一律先按小月发放,等新日历到了,一看如果有大月,再给补回来。
直到今天也是一样,从汽车上路大小号怎么限行?到一年哪几天放假?怎么调休?这都是政府的一项公权力。整个社会的作息、动静、行止的节奏,都是靠一张公认时间表来调节的。否则,包括老百姓的约会、节庆、赶集、婚姻,任何公共生活都无从谈起。
你可能会说,那西夏也没有必要非得要宋朝的时间表啊。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自己制订历法不就完了吗?可以是可以,但是历法的本质,是对周期性天文现象的预测,因为大家看到的都是同一个地球围绕太阳公转,这一圈叫一年,同一个月亮围绕地球公转,这一圈叫一个月。昼夜平分这是春分秋分,太阳照在南北回归线上,这叫冬至夏至。啥叫预测,就是你制定的这个历法,真的能预测,能跟头顶上的天象对得上。你说初一,月亮真得看不见;你说十五,月亮真得圆;你说今天冬至,那后面的白天确实得越来越长;你说哪天日食月食,老天爷真得能帮你作证才行。对,历法这个事,不是随心所欲可以订的,它不仅有技术门槛,而且行还是不行,拉出来遛遛,所有人都可以拿天象做验证。
这套观测天文现象的方法,不是所有文明都掌握了的。这也就是为啥能不能制定出精确的历法,成为了衡量人类早期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太平广记》里面就记载了唐太宗的一个故事。太史令李淳风,就是负责推算历法的官员,有一次对唐太宗说,我预测马上会有日食。因为牵涉到占卜,太宗不高兴了,要是到时候没有,你就说怎么办吧?李淳风倒也够硬,回了句,如果到时候没有,我就自杀谢罪。结果到了那天,唐太宗就在皇宫里等着看,没看见日食。他就跟李淳风说,来吧,我放你回家一趟,你准备跟你老婆孩子告别吧。李淳风说,别急,等着太阳的影子到了墙壁上,才到时候。诶,最后的结果跟李淳风说的分毫不差。你看看,不仅验证容易,而且双方都不会有争议,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没有半点含糊。
即使是大宋,虽然历法技术相对先进,但是也无时无刻不面对这种验证压力。就拿这次颁给西夏的《崇天万年历》来说,这部历法是从宋真宗的时候开始研发的,天圣元年,就是宋仁宗上台的第一年就出了成果。结果当年说有日食就没能验证,老天爷没给面子,只好又回炉再改。后来又遇到过预测不准日食的情况,只好换用了一种“明天历”,结果用了三年,明天历预测月食又不准,只好又改回到崇天历。
顺便多说一句:“可验证”这个特性带来的好处非常大,因为可验证,所以中国古代历法非常开放。举个例子,明朝末年的时候,很多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朝廷里面就分成两派,一派以徐光启为首,主张用西方传教士的技术来推算。另一派就是保守派,觉得徐光启就是在妖言惑众,还是老祖宗的办法最好使。崇祯皇帝就说,那验证啊,比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前后一共比了八次,无非就是日食月食行星运动,看谁预测得准。结果呢?比了八次,结果是八比零,都是徐光启这一派赢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本土历法就融入了西方历法的很多算法,我们今天的农历,就是这么一路演化来的。你看,因为可验证,一翻两瞪眼的事儿,保守派也没得可保,省了很多无谓的争执。
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南怀仁和杨光先的冲突。那是另一个精彩的故事。1664年的事儿,我们《文明之旅》按照计划,会在 12年后说到它,敬请期待。
好,说回到大宋和西夏。要说当时的历法技术,大宋毫无疑问要远超西夏。所以,颁赐历法这个事儿,不仅是大宋对西夏的要求,也是西夏对大宋的需求。从一个历史细节就可以看得出来。半个世纪后,到了1097年,那是宋哲宗的时期了,双方形势又开始紧张,宋朝这边的一个举动就是停止颁赐历法。到了宋徽宗上台,才恢复。所以你看,“颁赐历法”和“要你称臣”不是一个性质的行动。从来没见过大宋皇帝主动不要人称臣的,但是主动收回历法,多少带有一点惩罚的意思:卡你脖子,看谁求谁?
中原王朝这边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历朝历代,不仅自己要内部统一历法,而且要垄断技术。有学者统计,中国历代王朝,基本上在开国的时候,都会颁发禁令,禁止民间研究历法。宋朝一向号称推崇仁政,但是对这种关键技术也绝不含糊。太平兴国二年,也就是宋太宗那会儿,把全国 351 个懂天文的人抓到开封,在里面挑了 68 人送到官府里做事,其他人全部把脸刺上字,发配海岛。到了宋真宗的时候就更严,如果敢偷藏这方面的禁书,抓着了就处决。举报相关嫌疑人,赏十万钱。这样的严刑峻法,有士大夫反对吗?没有。岳飞的孙子岳珂就说过,为了技术保密,不得不这么做啊。
大宋朝只有一次放开了禁令,也是因为“不得不”。那是靖康之变的时候,女真人攻破开封城,见着天文仪器就搬,见着天文官员就抓,为的就是抢走推算历法的技术。从开封到燕京,一路上很多仪器都毁掉了,剩下来的,也因为两地相差千里,地势也不一样,没法用了。而宋朝这边,宋高宗到了杭州之后,没有天文官员可用,只能解除禁令,从民间招人。宋朝这还算是幸运的,想找的时候还能找到。明朝因为初期杀懂天文的人杀得太厉害,到了明孝宗的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真没人,还是都被杀怕了,反正官府怎么征召,都找不到会算历法的人。
你看,历法这个技术,在古代就是这么敏感。
你可能会说,如果自己研制历法那么难,那西夏就不能搞一套宋朝的历法,然后假装是自己的,换个包装接着用吗?就像今天的软件套壳一样。确实可以,而且在很长时间里,西夏就是这么干的。我们今天在西夏的黑水城遗址考古,发掘出西夏后来自制的历法,可是和当时南宋的历法一对比,在历法格式,月份大小,以及每个月的第一天是哪天,简直是一模一样。
但是请注意,那是在南宋。双方的疆域已经脱离接触了。如果是在北宋时期,西夏如果非要这么做,也不是不行,但是,双方之间毕竟还是有人员往来,大家一对,哦,我们号称的西夏自己研制的历法原来和你们那边一模一样啊?这个是瞒不住的啊。
好,如果西夏接受了大宋颁赐的历法,用上了先进技术,那会有什么下一步的后果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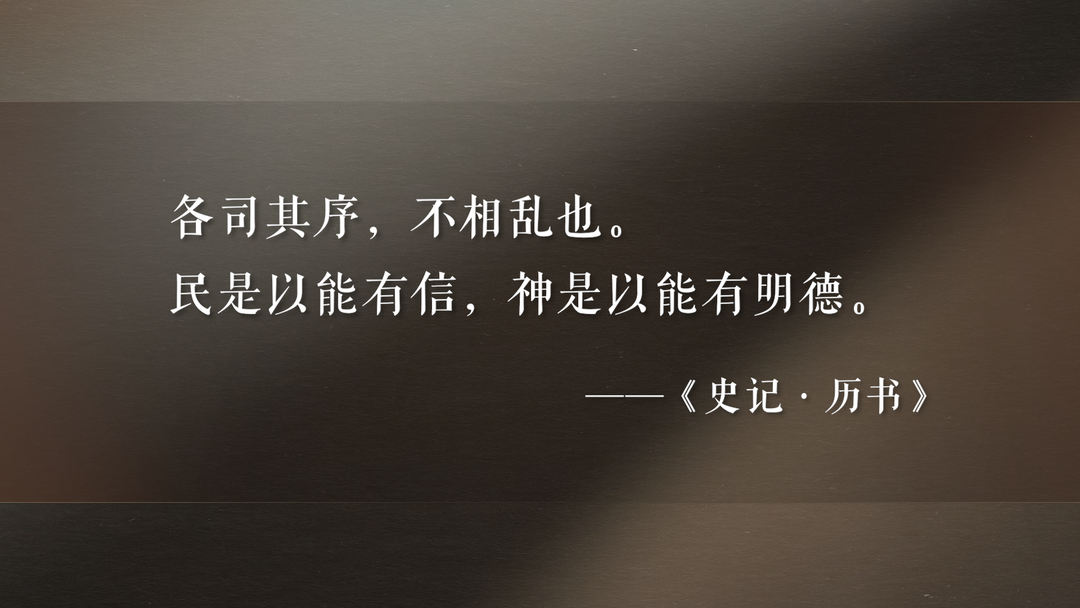
合法性的时间
刚才说的,是历法的工具性,也就是实用性。但是,如果这么理解历法,就还是有点浅。
过去一提中国古代的历法,好像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农耕民族,历法是种地生产的需要。没有历法,容易误了农时。江晓原老师的这本书《通天——中国传统天学史》里面就澄清了这个误区。你想,中国古代指导农业,有24节气,它在西汉初年的《淮南子》里面就已经全部出现了。2000年了,没变化。这说明啥?说明节气就是说个大概,不用再往前做精细化迭代了。因为农时嘛,不需要那么精准,误差个几天,影响不了什么。而且你看,24节气里面,只有四个节气,春分、秋分、夏至、冬至,那是含糊不得的,必须上应天象。其他二十个节气直接与季节、气候及物候有关,比如雨水、惊蛰、清明、谷雨、立春、立冬、大雪、小雪,这些用不着精密的历法推算,它们更多是来自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
那既然历法和农业的关系不大,为什么中国古代那么重视历法呢?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司马迁的《史记》,我们一般津津乐道的就是它那112篇的本纪、世家和列传。里面都是有趣的故事嘛。但实际上,《史记》里面还有非常重要的“十表八书”,其中八书里面有三篇,《律书》、《历书》、《天官书》,都是讲天象、历法之类的东西。我们这些现代读者觉得没用,也看不懂,所以就自动忽略了。实际上,古人对这个部分非常非常重视,《史记》的很多篇目,后来的二十四史都没有继承,但是,这三篇跟天象历法有关的,后来的官修史书,几乎都保留了,变成了“天文、律历、五行”的“天学三志”。我们现在讲宋朝,《宋史》里面,这“天学三志”就占了37卷,几乎是十分之一的篇幅。
为什么这么重视?一言以蔽之,因为它牵涉到皇权的合法性。
马克斯·韦伯对国家有一个定义,国家就是垄断了暴力使用权的机构。但他这说的是现代国家。在古代中国,国家还要垄断一样东西,那就是和老天爷的沟通。这有一个名词,叫“绝地天通”。意思就是把上天和地上的沟通渠道给断绝了,但不是真断,而是掌握在特定的人手里。谁啊?当然就是君主和他身边的知识分子啊。通过掌握了和天沟通的渠道,进而掌握了和天沟通的解释权,再进而就可以对人间万事赋予意义,再进而为人间所有的秩序立法。
那这是迷信吗?不能简单地这么说。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是很难体会古人的那种心境的。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先生在这本《回家记》里就讲过,他说古人的生活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对时空之外的东西感到恐惧和焦虑。我看不到的地方,我死之后的世界到底什么样?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心理压力,那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减轻,那就是在地上建设的东西,要符合天象。比如按照我理解的天道来建设城市。比如,城市往往以北极星定位,城墙以东南西北的基准方位而建,宗庙和社稷位列中轴线两侧。如果你有兴趣翻翻中国古代的筑城史,几乎每座重要城池,都或多或少地讲究和上天星象的对应。这叫“象天法地”。人间的事物都太短暂、太脆弱了,如果能和上天有一点点相似,可能也会帮助我们贴近永恒吧。大家心里好受一些。
历法也是同样的道理。我能掌握一点日月周行的规律,我就接近永恒,我就能垄断和天对话的权力。
比如说,中国古代历法特别重视的就是日食。按照天人感应的说法,太阳就是皇帝。那日食来了,太阳突然被遮盖起来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两种解释都行。说皇帝干得不好,上天示警,所以皇帝要反省,这是一个说法;说有奸臣蒙蔽皇帝,就像乌云遮盖了太阳,也行。不管哪种说法,最好都能提前知道,那皇帝就可以预先做一些准备啊,斋戒,或者干脆不吃饭、不听音乐,或者要求大臣批评一下朝政,求直言等等,反正皇帝摆个自我反省的态度。这就是在告诉天下,一切尽在掌握。我的上级批评我了,但是我知道怎么办。

上古的时候是发生过这样的事儿的,掌管天象的大臣因为喝醉了酒,没能预报一次日食,居然就被杀了。而且按照那个时候的规矩,报早了也是杀,报迟了也是杀。你就说那个时候的君主,为了这个事儿,心态多容易崩吧?现在你理解了前面我们说的那个故事了吧?唐太宗为什么听见太史令李淳风说要日食,马上就不高兴,就想杀人。
到了北宋这个阶段,历法这事儿就变得更敏感一些。为啥?因为还有其他政权,也就是大辽在和大宋竞争合法性。
历史上有这么个事。“澶渊之盟”不是规定了,逢年过节辽宋双方要互派使节吗?神宗朝有一年冬至,大宋使团一过边境,就遇到一个问题。辽朝这边的接待人员就问,说怎么回事?你们宋朝历法里的冬至,比我们辽朝的冬至要早一天,谁是对的?这个问题,往小了说,是历法对错的技术问题。往大了说,就是政权合法性谁更胜一筹的问题。
顺便解释一下,为什么冬至这么重要?因为这是皇权合法性的三个支点之一。中国古代,国家最重视的就是三大节,元旦、冬至和皇帝的生日,也叫圣节。你看,元旦是一年之始,算是历法的开头;冬至是阳气初生,北半球的日照从此越来越长,算是天道的开头;而圣节,生日嘛,算是皇帝本人的开头。这三大节就把历法、天道、君主突出出来了。而这次外交事件,出事就出在这一点也含糊不得的冬至上。
幸好,这个时候大宋使团里面有一个人,他叫苏颂,大宋著名的天文学家,他就出面解释,说这是一个非常细节的技术问题,不就差一天吗?你想啊,差一刻钟,如果正好在子时,两天相交的时刻,在历法的推算上,也就差了一天。不是啥大问题。各家用各家的历法就行了。这才算勉强糊弄过去。你看得出来,双方在这个问题是很较劲的,背后是合法性竞争嘛。
那你说,一旦出现错误,改了不就得了吗?也没有那么简单,还是因为牵涉到合法性的问题。
比如在后来的宋神宗时期,沈括,就是写《梦溪笔谈》的那个大科学家,他就发现,宋朝用的历法跟现实的偏差已经很大了,应该把当年的闰十二月改成闰正月。这在技术上讲是正确的,但是在政治上讲,不一定,这就引发了争议。为啥?因为不仅大宋自己用历法啊,还有很多小国都要奉大宋的正朔呢。人家都是按照大宋每年颁布的历法进贡的,你这临时一改,人家都乱套了。你大宋是大哥啊,连象征通天权力的历法都能搞错,威严何在?所以要谨慎。
说到这儿,我们再来看1045年,大宋给西夏颁赐历法这件事。你会发现,历法就像那个特洛伊木马。表面无害,但暗藏玄机。刚开始,把历法给你的时候,也许只是满足你的现实需要,但是这里面,还藏着一个合法性的疑问。时间一长,西夏的老百姓就会知道,能和老天爷沟通的,代表政权神性的那个部分,不是兴庆府里的西夏国主,而是远在开封城里的宋朝皇帝。
大宋朝能在这宋夏停战的1045年,为未来埋下这个伏笔,也许有妙用的伏笔,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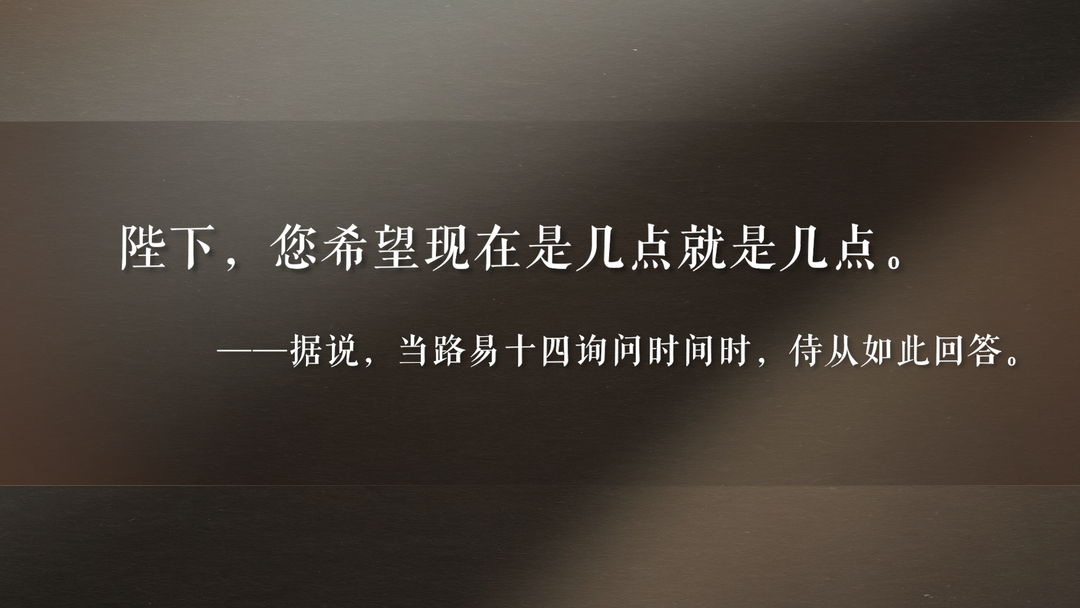
创造性的时间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话题再往前推进一层。大宋颁赐历法给西夏,其实还留下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利用对时间节律的掌控,来更进一步地影响西夏。时间表看似客观,但上面其实留下了很大一块创造性的空间。
举个例子。我刚才讲,中国古代官方重视的三个日子,元旦、冬至和皇帝的生日。你发现没有?冬至是根据天象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元旦的客观性就稍微差一点了。中国古代,有用一月、十一月、十二月,当一年开始的月份的。比如秦朝,一年开始的月份就是十月。哪个月是元旦,要看怎么规定,但是一旦定下来,也很难改。只有第三个日子,皇帝的生日,一个皇帝一个生日,经常改。这就是时间表上生生创造出来的日子。
那什么时候皇帝生日变得这么重要呢?是从唐朝开始的,具体说,是唐玄宗。开元年间,唐玄宗把自己的生日,每年的八月初五定成千秋节。各地都要庆祝,全国放假三天。你看,皇帝个人的日子,突然嵌入到了时间体系当中,而且变成全国性的节庆,很明显,这是一个强化皇权的动作。
要知道,在南北朝之前,中国古人是没有庆祝生日的传统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不符合儒家的伦理观念。你想啊,儿的生日,母的难,如果你父母不在了,生日那天想起父母,你应该难过才对啊,怎么还能喝酒庆祝呢?那为什么后来又过了呢?其实是受到佛教的影响。因为佛教从东汉开始,就有在释迦牟尼生日那天搞纪念的传统,四月初八佛诞日,又叫浴佛节,宗教气氛很浓,越搞越盛大。
所以你明白唐玄宗为什么要凑这个热闹了,为了让自己和佛一样,也沾上点神圣色彩。你想啊,为皇帝贺寿,对民间的普通老百姓来说,隔膜得很。但是他们知道,第一,这天要热闹一下,有酒有饭,所以是一件好事。第二,过去为佛菩萨过生日,要盛大庆祝一下,现在又要为一个人过生日庆祝一下,这人即使不是佛菩萨,也差不离儿吧?
所以,唐玄宗过生日,越搞规模越大,不仅要喝酒要放假要娱乐,还要大赦天下、免除天下租赋、封官、赏赐,把能想到的所有好事儿都堆到这一天。目的很简单,就是让老百姓知道,好事都是和皇帝个人关联在一起的。
你看,时间表这个东西很有意思。看起来川流不息,客观公平。但实际上,有心人可以在时间表上选择一个点,进行创造性地塑造,往里面添加自己想要的意味。最终,时间表会变成他影响世界的一枚工具。
到了宋朝,给皇帝过生日,就更加制度化了。它不仅对内彰显皇权,圣节还是一种很重要的外交博弈手段。
你想啊,皇帝过生日,我们要庆祝,你们这些友好邻邦,不来贺个寿,合适吗?你来了,那就是把我们皇帝的神圣性往你那里传播了一下。大宋和大辽,很多次利用这个工具搞外交战。
我举个很小的例子你感受一下。宋仁宗去世,宋英宗继位那一年,辽朝给宋朝皇帝贺寿的使团来了。这两国,原则上是兄弟之国,但是谁兄谁弟,就要顺着当年签订澶渊之盟时候的宋真宗和辽圣宗的辈分往下捋。捋到宋仁宗的时候,辈分儿大,所以,辽朝皇帝要管宋朝皇帝叫伯父。现在好不容易把伯父熬死了,这下两国皇帝该平起平坐了吧?辽朝的使团就留了个心眼,本来准备瞒一下的,结果一不留神,被宋朝这边的接待人员把真话套出来了,原来辽朝皇帝岁数比宋英宗要小。他们这个后悔啊,完蛋,又要称宋朝皇帝为兄了。
从这个故事里,你就知道了,第一,皇帝个人之间比大小,就是国家之间比大小。第二,皇帝的生日,如果国家需要,也不是不能编一下的。要不辽朝使者为什么要后悔呢?肯定是准备要编的嘛。
刚才说的这些例子,都在说明:历法,时间表,看起来很客观,但是上面也留下了很多人为操作的空间。如果善于利用的话,这些空间是可以用来做政治博弈的。
回到宋朝和西夏:你西夏用了我宋朝的历法,那我皇帝的生日,是历法上载明的重大节日啊,你要不要来朝贺一下?为了保证你来,宋夏签订协议的时候,就已经注明了,其中有一部分经济利益,是要在你来给我大宋皇帝贺寿的时候,我回赐的礼物。不少呢:银一万两、绢一万匹、茶五千斤呢。你夏国君主过生日,我们也给,不过那就少很多了,银只有2000两,丝绢什么的,加一起给3000匹吧。
你看,这就决定了两件事。第一,你就是比我矮一等,低一格儿。这事不是抽象的。是写在日程表和根据日程表举行的行动上的。年复一年强调这件事。第二,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不来,不来就没有这笔经济利益啊。更重要的是,大宋朝还在这里埋下了又一个伏笔:我们皇帝过生日,你如果不来朝贺,我不想打仗的时候,那就省了一笔钱,我想打仗的时候,哈哈,那可就是一个战争理由啊。老大过生日,你不表示,想造反啊?
这事后来真的就发生了。宋神宗的时候,宋朝判断,火候差不多了,可以灭西夏了,出兵的理由就是这个。说最近西夏不知道咋回事,朝廷给他们回赐的礼物,他们居然没人接收。肯定又想以下犯上了呗?加上又有骚扰我边境的事儿,那我可就打了啊。
后来到了宋哲宗上台的时候,大宋不想打了,那就再允许你西夏给皇帝贺寿吧。后来又觉得可以对西夏动手了,就又拿出这个理由开打。双方就这么拉拉扯扯,一直到北宋突然被金朝灭亡。
必须得说,越到北宋后期,宋朝就越有对西夏的战略主动权。在时间表上,给西夏规定了一个必须来给皇帝贺寿的日子,这确实成了宋朝操控局势的一个工具。
你看:你用了我的时间表,我在时间表上创造一个节日,我的节日可以操控你的行为,你不受操控就会承受后果。这是一根多么隐秘,但又是多么有效的因果链条啊。
时间是一种权力,这个效应越到现代社会就越明显。现代社会之所以让很多人觉得失去自我,就是因为人失去了对自己时间的掌控。
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说,“一切都不是我们的,而是别人的,只有时间是我们的财产。”但是到了现代社会,情况倒过来了,我们可以假装很多东西是我们的,房子、车子、各种消费品,但是唯有时间不是我们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每天打开日程表,有哪几项是真正自己决定的?今天早上我要开这个会吗?下午我想见那个人吗?不,只是因为它写在了我的时间表上;吃饭是因为我饿了吗?不,只是因为吃饭的时间到了;我要在人那么多的假期带孩子去那个游乐场吗?不,只是因为那天按规定放假;我要在双十一买东西吗?不,只是因为有一家公司发明了一个很有名的节日。近处的、远处的各种人,以柔软地、强硬地各种方式,给我规定了时间的使用方法。他们都是我不得不面对的权力。
你可以做个实验:你前面走着一个人,你不用跟他打招呼,你就随着他的脚步喊“一、二、一”,很快,你就能操控他的脚步,他就会非常不自在。
你看,无时无刻地活在他人决定的时间表里,我就失去了自由;反过来,始终坚持向世界输出时间的节奏,并用节奏带动他人,我就开创了秩序。从奉不奉正朔开始,自古以来,就有这种博弈,而且永远不会停止。
这就是我在公元1045年为你讲的发生在宋朝和西夏之间的一个有关时间的故事。下一年,公元1046年,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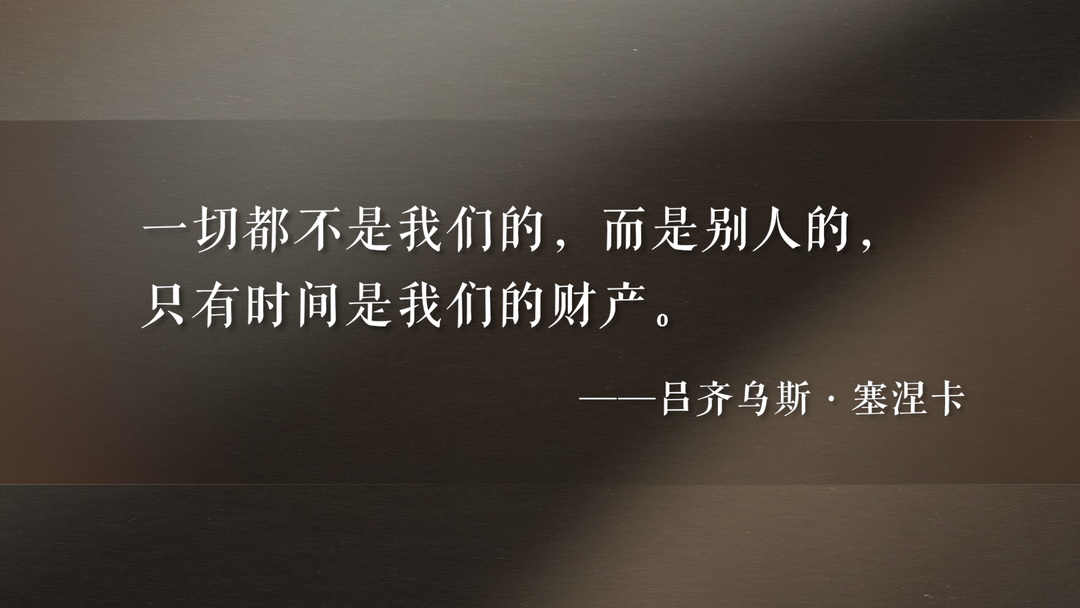
致敬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哲学家康德。
1045年这期节目,我们的主题词是时间。而康德,用一个传记作者的话说,他的一生过得就像规则动词一样,非常有规律,不管是起床、喝咖啡、写作、讲课、用餐还是散步,他都有固定时间。这个时间设定精准到什么程度呢?每天,当康德穿着灰色大衣、手里拿着拐杖,走出家门,朝一条菩提树小道走去的时候,邻居们就知道,三点半到了,根本不用看表,康德本人就是表。
一个大哲学家,为什么会过这么刻板的生活?
康德是个有目标的人,22岁的时候,他怀着满腔热情写道:“我已决定我的方向。我将踏上征程,任何事情都阻止不了我前进的步伐。”但你可能不知道,康德个子矮小,体弱多病,身材还有点畸形,一边肩膀比另一边高。他自己对身体状况非常清醒。正因为定了明确的人生目标,为了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他就持之以恒地恪守自己制定的生活规则,比如不管是天气阴沉,还是乌云密布风雨欲来,他都雷打不动地按时散步;再比如用鼻子呼吸,为了做到这个,在秋天、冬天和春天散步的时候,他完全不跟任何人说话。于是,这位体弱的哲学家,竟然活到了八十岁,写出了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
你看,设定出自己的节律,坚定地坚持这种节律,就有水滴石穿的力量。而我们的《文明》节目,也是用同样的方式,致敬康德。
参考文献
原始史料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 年。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 年。
(先秦)王世舜译注:《尚书》,中华书局,2023年。
(战国)左丘明撰:《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
(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晋)陈寿撰:《三国志》,中华书局,2011年。
(南梁)颜之推撰:《颜氏家训》,中华书局,2023年。
(唐)房玄龄撰:《晋书》,中华书局,1996年。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 沈括撰:《梦溪笔谈》,中华书局,2022年。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2020年。
(宋)汪藻撰:《靖康要录笺注》,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
(宋)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
(宋)岳珂撰:《桯史》,中华书局,1982年。
(宋)佚名撰:《宋大诏令集》,中华书局,1962年。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2019年。
(明)王夫之撰:《读通鉴论》,中华书局,2022年。
(明)李东阳撰:《大明会典》,广陵书社,2007年。
(明)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89年。
(清)吴广成撰:《西夏书事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清)龙文彬撰:《明会要》,中华书局,1998年。
(清)徐干学等撰:《资治通鉴后编》
专著论文:
江晓原:《通天:中国传统天学史》,中华书局,2024年。
韦兵:《完整的天下经验:宋辽夏金元之间的互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
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万物皆可测量:1250——1600年的西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
杜君立:《现代的历程:机器改变世界》,天地出版社,2023年。
李筠:《中世纪:权力、信仰和现代世界的孕育》,岳麓书社,2023年。
塞涅卡:《塞涅卡道德书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
赵冬梅:《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
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商务印书馆,2019年。
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中华书局,2014年。
段义孚:《回家记》,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92年。
李范文:《“邦泥定国兀卒”考释》,《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4期。
宁欧阳:《外交与政治:论宋辽间的圣节交聘》,《暨南史学》,2023年第1期.
宁欧阳:《王化蔓延:宋王朝的圣节互动——以夏丽等国及边疆诸“蛮”为例》,《史志学刊》,2023年第2期。
宁欧阳:《唐宋诞圣节研究综述》,《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第44期。
郭绍林:《论隋唐时期庆生辰》,《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