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美国作家亨利·大卫·梭罗在其著名散文集《瓦尔登湖》中,描述了他在湖畔一片再生林中度过两年两个月又两天的生活和思考。彼时,美国的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梭罗虽在瓦尔登湖畔过着远离尘嚣的隐士生活,却敏锐地洞察到技术的发展反而使人们在思想和智力上出现了普遍的退化。在全书驰辩非凡的结束语中,梭罗一再地指出这一危险的病症——人们倾向于贬低复杂或具有多重解读可能性的思想,而更加青睐那些简单的观念。他写道:“好像大自然只能支持一种理解秩序……好像只有在愚蠢之中才有安全”;“我希望在某个没有界限的地方说话,就像一个睡醒的人跟其他睡醒的人说话”;“他们声称迦比尔的诗有四种不同的意义……但是,在此地,如果一个人的作品有一种以上的解释,那会被当作批判的依据”。在层层的铺排与递进中,梭罗祭出了一段非常梭罗式的诘问:
当英格兰努力治愈马铃薯枯死病时,难道就没有人去努力治愈更广泛、更致命的脑腐吗?(While England endeavors to cure the potato-rot, will not any endeavor to cure the brain-rot, which prevails so much more widely and fatally?)
在此,梭罗将“brain”和“rot”两个单词用一个短横线相连,创造了一个崭新的词汇——brain-rot(脑腐),以对应使马铃薯腐烂的枯死病。意味深长的是,这个词汇没有像大多数新生却生命短暂的事物那样随风飘逝,反而在其后的170年间久弥新。可以说,一部brain-rot的历史,背后隐藏着一部媒体发展史和技术迭代史,以及人们对它的反思史。如果从阅读的视角来观照,也可以说是一段阅读文化不断走向衰落的历史。尤其是进入以算法为核心的社交媒体时代,以短视频为代表的低质量内容层出不穷,手机、算法和多巴胺的闭环几乎无懈可击,brain-rot这个词汇再次迎来了举世瞩目的高光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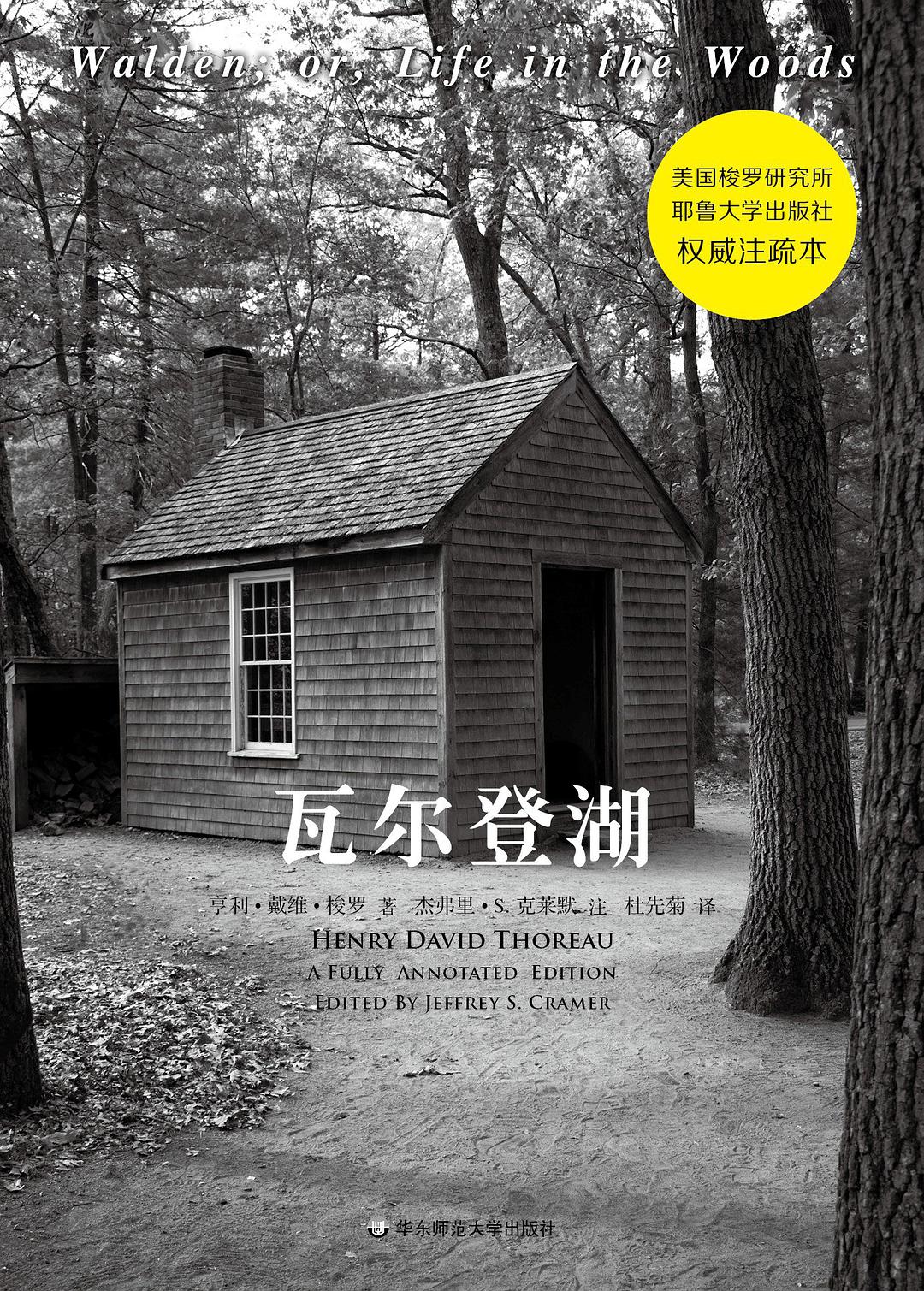
《瓦尔登湖》
这一切还要从梭罗出生的那个时代说起,那一年是1817年。那时的世界,依然被印刷术所统治,美国的主流媒体是铅字——也就是以报纸和书籍为主的印刷文字。移民到北美殖民地的英国人大多来自英国文化教育程度较高的地区或阶层,他们本身就有读书的习惯。到了美国之后,他们会在当地建立图书馆和学校。英国和北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关系为美国带来了大量的书籍——艺术类、科学类以及文学类的书籍,这些书籍大大地满足了当时人们的需要。这一情形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印刷品的广泛传播形成了一种没有阶级之分的生机勃勃的阅读文化,而没有像英国那样出现只为少数人所占据的文化贵族。
19世纪上半叶,美国各类图书馆的数量激增,《汤姆叔叔的小屋》(1851)在出版的第一年就发行了超过30万册,当时美国的人口只有7000多万。不仅如此,美国人还喜欢听演讲,这使得演讲厅得以普及。受印刷文字的影响,演讲者大多会采用书面语和复杂的句式,演讲或讨论的内容大多也是严肃的,而且每次演讲动辄几个小时。然而,听众们却听得津津有味,他们具有丰富的背景知识,包括历史事件和复杂政治问题的知识,而且具备理解复杂长句的能力。如果听到什么精彩之处,他们甚至会情不自禁地鼓掌。作为一个新兴文明,美国比任何一个社会更痴迷于铅字以及建立在铅字基础上的演讲术。
然而,这一切却随着电报技术(1837)的发明而摇摇欲坠。可以说,电报技术的横空出世将整个人类文明分成了两个阶段。在此之前,信息传播的速度就是马车的速度,是船舶的速度,是火车的速度,也就是大约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正是这种“慢”让我们有时间阅读,有时间思考,有时间甄别信息,有时间依据信息采取行动。而电报的出现抹除了所有的界限,消灭了地区的概念,把所有人纳入了同一个信息网络。由此,我们能知道几千公里外发生的重大事件,我们能向远方的家人和朋友传达平安和思念。然而,电报技术也使得报纸的财富不再取决于新闻的质量或用途,而是取决于这些新闻来源地的遥远程度和获取的速度。还是梭罗,最先感知到了这一技术带来的“信息过载”:
我们匆匆地建起了从缅因州通往得克萨斯州的磁性电报,但是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可能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需要交流……我们满腔热情地在大西洋下开通隧道,把新旧两个世界拉近几个星期,但是到达美国人耳朵里的第一条新闻可能却是阿德雷德公主得了百日咳。
就这样,电报的发明让美国变成了一个“社区”,也彻底改变了报纸的面目。从此以后,报纸上的中心位置不再是当地新闻和那些没有时效性的内容,而是战争、犯罪、交通事故、火灾和水灾。这些新闻的特点是标题耸人听闻,结构零散,语言前后不连贯,且没有特别的受众。而且,这些新闻的形式类似口号,容易被记住,也容易被忘记。往往一则新闻与另一则新闻之间可能毫无关系。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到报纸给人带来的“脑腐”风险:人们似乎读了很多东西,又似乎什么也没读。究其根由,电报让信息变成了碎片化、毫无关联的符号,人们的时间和注意力开始被撕裂。
如果说,电报技术带来了报纸内容的惊人变化,为阅读文化在总体上走向浅薄埋下了深深的隐患;那么,20世纪上半叶电视的诞生和普及,则是要将阅读文化整个连根拔起。因为,电视所代表的电子图像的革命不再是文字媒介的衍生,而是颠覆性地将“看”取代了“读”,并成为我们进行判断的基础。或许有人会问,难道看电视时就不能很好地思考吗?答案是几乎不能。因为电视上每个镜头的平均时间只有3.5秒,我们的眼睛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屏幕上一直有新的东西注入你的眼睛和大脑。更重要的是,“好电视”最重要的图像要吸引人,它在本质上是表演的艺术,而不是思考的艺术。
电视的这一本质决定了它必须满足人们视觉快感的需求,这一切正是娱乐业兴起和不断强盛的原因。从古至今,人类的生活确实需要娱乐,这本也无可厚非。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人们对于电视媒介的“脑腐式”热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它让我们生活中的政治、宗教、商业、教育、法律和其他重要社会事务的运行方式全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留给我们思考的时间越来越少。最后,当人们环顾四周时,他们惊愕地发现无论是电视屏幕上还是人们的生活中,都渐渐只剩下了一种声音——娱乐的声音。
对比阅读书籍和看电视两种行为,人们对于电视传递的信息处在一种被动的接受状态,这些图像化的信息洪流永不停歇,抓住人注意力的东西往往不是知识、思想和情感,而是充斥着感官刺激的娱乐;真正的阅读则是自由、自主的,阅读时可以随时停下来思考,甚至做笔记,但电视显然无法这样,对话也就无从谈起,这是由它的动态本质所决定的,它容不得你思议。更糟糕的是,一条足以让你感动落泪的新闻之后,可能紧接着一条娱乐性十足的爆料,这会让你的思想一片空白,情感一片混沌。
说到底,尽管都是人类的创造物,书籍和电视乃是两种迥然不同的媒介。事实上,所有的媒介和工具都会反过来塑造、影响乃至奴役人类,更准确地说,是人类的大脑。德国人尼采或许是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之一。1867年,23岁的尼采收到了挚友科泽利茨的一封信,信中说:“(你)滔滔不绝的雄辩变成了简短的格言,字斟句酌的推敲变成了朴实的‘电报风格’”。对此,尼采在回信中写道:“我在音乐和语言方面的思考经常会取决于纸和笔的品质……我们所用的写作工具参与了我们思想的形成过程。”在此,尼采已然触碰到了人脑高度可塑性这一当时还不为人知的重大秘密。
1884年,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提出了一个惊天猜想:“神经组织看起来被赋予了极强的可塑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管是外力还是内力,都能让那种结构变得跟以前有所不同。”这一观点的爆炸性不亚于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向外界宣布人类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直到1968年,这个天才的猜想才被神经科学家梅尔泽尼奇的开创性工作所完全证实。在这项意义深远的实验中,梅氏首先切断了猴子手上的某些神经,发现猴子的大脑一开始出现混乱;但是几天过后,他惊奇地发现猴子的大脑完成了自我重组,其神经路径可以自行编织成一张新地图,其结果与猴子手上新的神经排列相一致。于是,尼采在一百年前所隐约感觉到的秘密最终揭开了谜底,那就是技术、媒介和工具可以重塑我们的大脑和思维——从书籍到报纸再到电视,每次技术与媒介的革命,都会引发人们关于“降智”(其实是“脑腐”的另一种表述)的关注与讨论。
其实,当柏拉图用笔写下他那些哲学名篇之时(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只相信记忆和对话,而拒绝用笔写作),当尼采用球形打字机打字写作之时,当短视频时代的人们抱怨自己再也无法阅读任何长篇的文字之时,他们所碰触到的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这个中心主题。我们怎样发现、存储和解释信息,怎样引导注意力,怎样调动感觉,怎样回忆,怎样遗忘,这些全都受到技术、媒介和工具的影响。技术、媒介和工具的使用让一些神经回路得到强化,而使另一些神经回路逐渐弱化,让特定的心智特点日益彰显,而让别的特点趋于消失。表面上,我们在使用和摆弄工具;实际上,工具在塑造我们每一个人。
20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了电视文化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教授于1985年出版的《娱乐至死》一书(大陆于2004年推出了首个中译本,封面画着只有身躯没有脑袋的一家四口,围坐在电视机前,在隐喻意义上与“脑腐”一词形成了完美的呼应),将电视文化引发的心智灾难剖析得入木三分,并产生了全球性的广泛影响。然而,波兹曼在全书的结尾处却给出了悲观的结论:让人们就这么放弃电视是不可能的。对此,他举例道:1984年,康州一个图书馆倡导“关掉电视”的活动——这次活动的主题是让人们在一个月内不看电视。然而,电视媒体对这个活动进行了广泛的报道,人们很难想象活动的组织者没有看出自己立场中表现出来的讽刺性。波兹曼本人也感同身受,他写道:“有很多次,有人让我到电视上去宣传我写的关于反对电视的书,这也是同样的讽刺。这就是电视文化的矛盾。”

《娱乐至死》
2003年,尼尔·波兹曼教授逝世。之后的二十年间,整个世界再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波兹曼教授活在当今时代,他一定会惊叹社交网络几乎重新定义了他口中的媒介文化。时至今日,年轻的一代人已经不像过去的人们那样沉溺于电视文化,他们有了更具吸引力的东西——社交媒体。2023年,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人均单日触屏时长为435分钟,已接近理想的睡眠时间。人们已经习惯了每天在各大平台间来回切换,浏览新闻、刷短视频、点餐购物、互动点赞,每个平台的功能与内容各有侧重,指尖滑动中,用户也在切换扮演的不同角色。然而,网络上的低质量内容乃至垃圾内容过多,各种编造的短视频剧本频繁收割情绪,算法加剧着偏听偏信的“信息茧房”。人们手机刷得越多,精神似乎变得越发空洞,也正是由于精神的空虚,更加剧了对手机的依赖。或许,这真的是一种病。
2024年12月2日,“脑腐”(brain rot)当选牛津词典2024年度词汇,让这个梭罗170年前创造的词汇再次迎来全球性的关注与热议。按照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官方解释,所谓“脑腐”,即一个人精神或智力状态被认为出现了衰退,形容因过度浏览网上低质量内容(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而导致的精神负面影响。牛津词典主席卡斯帕·格拉斯沃表示,“脑腐”一词揭示了虚拟生活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以及我们如何利用闲暇时间,这似乎标志着人文关怀与技术发展之间的新碰撞篇章。有意思的是,“脑腐”击败的另一个强劲对手是“垃圾内容”(slop),两者似乎构成了因果关系。我们的双眼被钉在了小小的手机屏幕上,看了太多的“垃圾信息”(slop),才诱发了“脑腐”(brain rot)的产生。
如今的每天每时每刻,网络上永远在不断更新各种slop,以至于很多人如果不学网络梗,就会觉得被社会所抛弃。你刚刚搞明白“珂学”,大家突然就不玩了;然后你又专攻“麦学”:麦琳为什么买熏鸡?李行亮太可怜了!李行亮和她合好啦?必须抵制!一分钱都不能让麦琳赚去!……再然后,你隔半年回头一看,已经无人关心“猫一杯”是谁……读了很多信息却没有学到知识;吵了很久却一直被别人设置议题,成了流量的耗材,只觉得大脑曾经被赛博的海水泡沫淹没过、翻涌过,大潮退去什么都没有剩下,只留下的只有越来越重的“脑腐”症状。
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今年9月出版的新书《智人之上》中指出,算法发现充满仇恨的阴谋论更能提升人类在社交平台上的参与度。所以,算法就做出了一个致命决定:传播愤怒,传播阴谋论。而这些基于愤怒、阴谋论的讨论,其实是最没有意义,也最不可能达成共识,最无助于推动社会进步的。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些当代“脑腐”神器,明明是毫无意义的东西,却因为低层级情绪的撩拨,算法的精心推荐,自我的情感投射,占据了赛博的风暴眼。互联网高歌猛进了20多年之后,我们似乎对丑陋的赛博世界渐渐达成共识。信息洪流奔涌向前,我们的大脑成了献祭“流量拜物教”的贡品。
然而,技术的迭代永远没有终点。眼下兴起的AI浪潮,正逐渐渗透生活各个领域,“润物无声”改变着未来世界的格局。其实,入围的年度候选词汇slop一定程度上已经展现了AI对整个社会的巨大影响。按照官方解释,Slop指的是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艺术、写作或其他内容,这些内容被随意或大量地在线共享和传播,通常内容质量较低、缺乏真实度或准确性。身处智能爆炸的时代,人们接触到的信息、吸收到的信息、真实需要的信息,三者之间的鸿沟正不断扩大。普通人如何在网络这片“信息汪洋”中汲取养分,拒绝“脑腐”?重返“原始时代”并不现实,我们必须学会同芜杂的信息共处,尽可能保持独立思考尤其是深度思考的能力。当然,适当的“数字戒断”,生活中的刻意留白,未尝不是疗愈自我的解药,正如卡尔·纽波特在《数字极简》中所言:
(数字极简主义是)一种技术使用理念,将线上时间用于少量经过谨慎挑选的、可以为你珍视的事物提供强大支持的网络活动上,然后欣然舍弃其他的一切。







